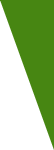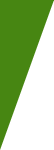一个来自南洋华侨对种族、人情薄幸的叩问,一个来自北美女性对宿命的细腻述说,本届中山杯华侨华人文学奖,把大奖同时颁给了李永平的《大河尽头》和张翎的《阵痛》,不同的风格,不同的视角,却都是一份对生命的敬重与关照。追溯大河尽头,那是我们曾经失去的原乡,大河向下,那是浩瀚的大海,在那里,一切都归于平静,我们将获得永生。
第三届“中山杯”华侨华人文学奖大奖、长篇小说《大河尽头》作者
一九六二年仲夏,婆罗洲沙捞越,一名叫永的华裔少年加入一场卡布雅思河的探险。大河苍茫,日头炎炎,永在船上遇到探险家兼沙捞越博物馆馆长安德鲁辛普森爵士,面对探险队的目标——圣山峇都帝坂,土著达雅克人心目中生命的源头,永充满好奇,辛普森爵士却淡淡地回答:“生命的源头,永,不就是一堆石头、性和死亡。”
这段对话,成为开启永探险之旅的预言,也成李永平对于原乡及生命原初意义的叩问。
当他的父亲——一位广东揭阳县灰寨镇的读书人,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跟随者一帮“卖猪仔”乘坐着压舱底的轮船,漂洋过海,去往马来热带雨林之中时,他从未想过今生就将与祖国永别。读书人想的是经世济人,攒够了钱,终究要风风光光回到“唐山”的。但时局动荡,他不得不死心塌地在异乡定居下来,而后有了李永平,以及他的七个兄弟姐妹。
李永平把父亲称之为“浪子”,而自己则是“游子”。在到底成为“马来西亚人”还是“中国人”的挣扎之中,敏感的他一直有着撕裂之感,以致于十分喜爱体育运动的他总是不敢看决赛时马来队和中国队的比赛,尤其是林丹和李宗伟的比赛,“我不知道支持谁,心里充满了怨恨。”
混沌之中,台湾“收留”了他,他说自己有两个故乡:一个生他、养他,一个在他人生的十字路口伸出双臂,让他在世界上有个安身立命之地。可是他的内心还有另一位娘亲,是他记忆中,父亲在信纸上反复写的那个地址——广东省揭阳县灰寨镇,是他童年乡里们口中的 “唐山”、“神州”、“华夏”——母亲中国。
《大河尽头》载着他回到了故乡,也为他“想象的乡愁”搭出了华丽的空间,火热的赤道、神秘的大河,混合着热带雨林的湿热与诱惑,对大河尽头的溯源,也不再只是乡愁的溯源。殖民主义对人的蹂躏、人在“中邪”状态下肆无忌惮的恶施,循环在不忍与不堪,救赎与堕落之间,李永平的欲望叙事一发而不可收拾。
大河尽头,到底是什么?生命的源头,到底是什么?《大河尽头》里似乎并没有对这个问题给出答案。李永平说,这是故意的。他说要让读者根据自己的体验和需要,提出自己的答案。他本人的答案据他自己说“很东方”,不外乎是个“缘”字。“这是贯穿大河尽头的母题。”
就像他补充说,他教书的第一所大学是台湾中山大学,他曾无数次梦想过回大陆,但第一次踏上祖国大陆的土地,居然就抵达他仰慕已久的孙中山故乡,而且是来领“中山杯”华侨华人文学奖。李永平把这一切归根于“冥冥之中自有天定”。
对话李永平
●殖民者的伤害是永远的痛
记者:《大河尽头》是一本带有自传色彩的书,我们在其中读到了很多女性视角,比如说姑妈、朱鸰这些角色,您意图通过他们去诉说些什么?
李永平:这跟我的成长经历有关,我的父亲是一位浪子,生下8个儿女后就去讨生计了,生活重担全部压在我的母亲——一位勤劳的客家女人身上,妈妈身体不好,还要默默地承受着许多苦难。另外我成长中亲眼所见原著民女性受到了殖民主义者的压迫和凌辱,我对她们报以悲悯的心态,并把这种悲悯扩大了所有社会中的女性。
记者:所以您的书中除了有对原乡的追溯,还有很多对殖民者的质疑?
李永平:《大河尽头》对西方殖民主义和所谓的“后殖民时代”的强烈批评,是我着力的一部分,可以说没有人像我这样书写对殖民者的痛诉。我在其中塑造了一个老律师的角色奥西,他是最有代表性的白人殖民者角色,白天和蔼可亲,用魔术哄骗孩童,晚上却干尽了各种龌龊的勾当。我在写奥西对原著民孩子的欺侮时,边写边哭,他们的哀痛和哭泣就像在我耳边。
听起来很荒谬却又是真实存在的,他们对于马来的掠夺是我亲眼目睹的。几百年来西方帝国对殖民地人们所造成的祸害,最大、最难弥补的,莫过于对一个民族灵魂所进行的有系统、有目的、有组织的摧残和消灭,在我看来,这是“造孽”。所以,我正在写的《月河三部曲》(分别为《雨雪霏霏》、《大河尽头》、《朱鸰说》)最后一部《朱鸰说》中,他就以非常残酷的方式死在了一个小女孩的手里——小女孩朱鸰替许许多多受难的人复仇,也替许多因为战乱和殖民而背井离乡的人复仇。
●离散的身份曾把人心撕裂
记者:写完这三部曲,是不是有种长舒一口气的感觉?
李永平:写完这部书,我的心灵受到了一次洗涤,无论是对殖民者还是其他,那些怨恨消失了,多年来的撕裂也和解了,很痛快,长舒一口气。
记者:但是《大河尽头》到底是什么,您也没有给与答案。
李永平:是的,每位读者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想要的东西。大河是一个意象,我有一个口头禅,“人生不外乎一个‘缘’字”,追溯生命的源头,这其实是贯穿大河尽头的母题。
记者:近年来,马华文学成为华语写作中令人瞩目的力量,您如何评价现在马华文学的写作状态?
李永平:马华文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像我们马来西亚华人第二代的写作中离散与漂泊的状态,在新一代马华文学作家中已经渐渐淡掉了,第二代华侨的心中始终有一座唐山,这样的情怀跟着他一辈子,但是新生代的作家在马来出生成长,已经渐渐融入了马来社会,我很替他们高兴,这样他们就没有痛苦了。而我刚好是夹在中间的一代,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这种撕裂的心态让我心里一直特别恨。为何这样的重担要让一个华侨少年来背负?后来我去了美国,本来有机会呆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教书,但是这种身份的撕裂,让我很敏感和纠结,所以最后还是回到了台湾,在写作中安身立命。
●只有中国和俄罗斯文学把祖国当做母亲
记者:除了写作,您也翻译了许多外国文学作品,您自己喜欢的作家是哪几个?
李永平:我在英国殖民地成长,从小接触西方童话,少年时代开始阅读西方小说,后来就读台大外文系,主修的是英美文学。但是,身为一个文学爱好者,我欣赏的并不是英美作家(马克·吐温除外,因为他写了一本我最爱的书《顽童流浪记》),而是俄罗斯文学,尤其是旧俄文豪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高尔基的作品,和苏联时代的一些小说。在这些作品中,我听到了一个民族发自灵魂深处的呐喊,还有其中的人道主义情怀,托尔斯泰在写安娜卡列宁娜被火车碾过后,悲痛欲绝,那样的悲天悯人,是一种震撼大地的哀痛。这种深层的东西,我在英美小说中找不到。而且全世界只有两个国家的文学语汇里,把自己的祖国当做母亲,一个是中国,另一个就是俄罗斯。
我之前翻译过奈保尔的《幽黯的印度》,几乎是一边翻译一边骂,有时甚至都想把书扔到窗外去,因为我看见了一个印度作家离开印度后,却以高高在上的姿态鄙视、嘲讽自己的国家,我非常不喜欢。写完三部曲后,我也想回到大陆到处走走,写一些祖国的文章,但绝对不是他这样的角度和态度。

 搜索
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