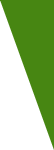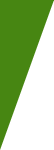第三届“中山杯”华侨华人文学奖大奖、长篇小说《阵痛》作者
从《金山》到《阵痛》,张翎先后拿走了两座华侨华人文学奖的大奖奖杯。首次来中山时,她的优雅知性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昨日重见,她身着一套简约的碎花长裙套装,风采犹胜往昔。在采访过程中,她如孩子般“呵呵”的笑声,不时会逗乐现场的采访者。不管是《金山》、《余震》还是《阵痛》,描述的都是人面对灾难和疼痛时的隐忍和爆发,张翎说,疼痛,通常是她写作灵感的起源,从这个角度来说,可以用“阵痛”来类比写作过程。
●女人在面对灾难时更坚韧
“阵痛”,原指女人临产时所遭受的疼痛,小说以此为隐喻,将女性的生命疼痛与历史创痛纠结在一起。张翎说:“这是我最多家族记忆的小说,题材来自我母亲的家族。”小说《阵痛》,描写了从1942年到2008年,三代身份、际遇迥异的母亲,经历了抗战、文革和“911”等重大历史事件的磨难,折射人世的风波险恶和生命的无常无奈,更彰显了母性洞穿一切苦难困窘的坚韧不拔。这是一个讲痛苦和希望的故事。最开始的初衷是想写女人,写生儿育女的故事,而在写的过程里面从家的概念延伸到社会的概念、国的概念,超出了她原先的预计。
“人类在世界每个角落时刻都在灾难里面,而女性总在以隐忍、卑微的方式活着,勇敢地活下来。”张翎说,《余震》和《阵痛》有相似之处,两部小说中貌似柔弱的女主人公在面对生命中出现的灾难时,都显示出了比男人更坚韧持久的力量。然而在《余震》里,灾难在李元妮王小灯母女两代人的身上留下的是内在的摧毁力量——地震无情地摧毁了人之间的信任感和对生活品质的期待。而在《阵痛》中,灾难表现在人身上的,是一种外在的发散型的能量。勤奋嫂在经历家破人亡的变故后,却依旧能把剩下的那点热量传给那些走进她老虎灶里的客人。在《余震》里,母亲是靠回忆往事来度过余生的,而在《阵痛》里,母亲是靠清洗前半辈子的记忆才能存活的。在《余震》里,李元妮是靠惩罚自己来生活下去的,而在《阵痛》里,勤奋嫂却是靠接济他人而活的。两部小说中都涉及了灾难和疼痛,但《阵痛》里的疼痛是带着希望的,正如女人生产时的阵痛。
对话张翎
●通过写作让心回归故里
张翎这些年一直生活在加拿大,书写的却大多还是故国的故事。在《阵痛》的创作手记里,张翎写道:“谨将此书献给我的母亲,我母亲的故乡苍南藻溪,还有我的故乡温州——我指的是在高速公路和摩天大楼尚未盖过青石板路面时的那个温州,你们是我灵感的源头和驿站。”
谈到这种写作视角,张翎举例说,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曾说过:“离去和流浪,都是回家的一种方式。他指的是一个人在远离故土之后,却通过写作回归故里。一个人无论在时间空间上离故土多么遥远,他这一生却从来不需刻意记住母语和故土,因为这两样东西是和血液融为一体,根本无法从身体里剥离的,“我虽然也写它乡的故事,但故乡的故事永远是占据灵感最重要位置的。”
有很多人提出,海外作家笔下的中国不像中国。对此,张翎的看法是:“从离开故土的时候起,我就已经失去了根。在新的国度里,土是浮土,我永远不可能再扎下那样深的新根。我从异国所书写的故土,似乎更像是两个国度中间的第三个国度,这个国度是我的想像世界,是真实的记忆在时空的间隔过程中所发酵衍生出来的东西。它是我个人版本的故土,虽出于无奈,我却希望我的视角由此而不同。”
●作品就像孩子会走自己的路
张翎认为,写作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过程,每一个作家观察世界和获取灵感的方式各不相同。她当过十七年的职业听力康复医师,这份职业使得她对战乱疼痛这些话题,会有一些特殊的感受,“我的病人中,有许多是经历过战争的退役军人,还有一些是从战乱灾荒地区逃到北美来的难民。他们所经历的灾难,是我这样在和平年代里出生长大的人所无法想象的。战争灾荒使他们失去了听力,也使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们的生命体验,极大的丰富了我作为作家的灵感,对我的写作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回顾我的创作历程,我似乎一直对两个主题情有所钟:一是人类远离故土,不懈地追寻理想家园,却以失望和幻灭告终。二是人性在被灾难推到极限时所表现出来的大善大恶,以及人面对灾难和疼痛时的隐忍和爆发。”张翎说,她这些年的一些作品《余震》和《阵痛》,似乎都和灾难疼痛相关。对于她来说,灵感的最初起源经常是以痛感开始的,最后的结果,是经历过痛苦之后的瓜熟蒂落。从这个角度来说,用阵痛来类比写作过程,也还算合宜。她也笑称写东西从来没想过得奖。“一部作品就像一个刚出生的孩子,它要走自己的路,走到哪我是不知道的。我不知道它能走着走着,就走到了中山,走到了华侨文学奖上。”谈及今后的创作,张翎说,“我无法对我将来的写作方向作出预测,但我会始终如一地尊重并且跟从内心的感动,尽量保护内心的感动在落实到文字的过程里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扰和污染。写作对我来说是一种充满激情的挚爱,尽管途程艰难,甚至经历了委屈和痛苦,但是我永远不可能舍弃它。”

 搜索
搜索